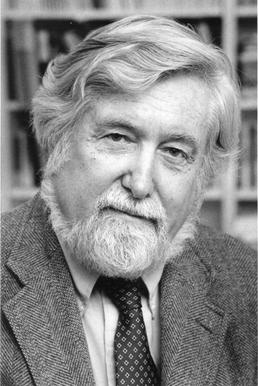國內所謂的「科技與人文的對話」,幾乎都是外行人的連篇鬼話,無助於溝通,反而平添彼此的誤解與刻板印象。關鍵在於:對話雙方沒有任何人真的認真跨越藩籬,去深刻地認識另一岸的文化與精髓。即便是英國 C. P. Snow 著名的演講 "The Two Cultures",也是充滿膚淺的鬼扯,因而招惹來著名文學評論家 F. R. Levis 的激烈抨擊。
對比下,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的經典著作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充滿「不讀可惜」的洞見,只是常被學術界誤讀。
底下我將仔細介紹這篇文章,並以他的另一經典 “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 作為輔助說明(兼佐證)的案例。
這篇文章其實是《論文寫作完全求生手冊》的〈附錄二、文化人類學的兩難〉(全文9,724字),但是值得所有文青閱讀,因此特地在此分享給更廣泛的讀者。
附錄二、文化人類學的兩難
文學的創作(譬如小說與抒情性的散文)截然不同於實證科學的論文,因為它毫無「以證據為本,以理服人」的意圖。至於文學作品的分析與評論,乃至於人類學的文化研究,則經常尷尬地介於兩者之間:往往有「以理服人」的期待,卻又跟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和論證原則有一定的差異。
文化人類學家紀爾茲大學時期主修文學與哲學,對此有著高度警覺。他毫不猶豫地認為文化人類學也是實證科學,卻又主張文化研究的本質是對於人類言行、活動的詮釋,迥異於物質世界的客觀研究;因此文化人類學必須有自己對於「研究」的看法,不能單純地承襲自然科學的方法,也不能只是承襲文學性的傳統。
底下將以文化人類家紀爾茲的代表性作品〈厚描:朝向文化的詮釋理論〉 和〈深層遊戲:關於巴厘島鬥雞的記述〉 為例,闡述他的論點,也藉此提醒讀者:在涉及人文領域與文化的研究時,本書各章所提的論文寫作原則可能需要進行一定的調整或限制,之後才能適切地應用。
文化研究是什麼:在自然科學與文學評論之間的擺盪
早期的民族誌不乏充滿偏見的主觀報導,為了竭力掃除這個弊端,人類學始祖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刻意模仿自然科學,主張人類學家要跟過去的成長背景徹底隔絕,以自然科學的客觀態度進行觀察與紀錄,讓民族誌的紀錄能忠於當地土著的想法與世界觀,有如自然科學在報導實驗室裡的現象。對此,紀爾茲期期以為不可。
他在〈厚描:朝向文化的詮釋理論〉(簡稱〈厚描〉)裡指出文化研究與自然科學有著明顯不同的方法和旨趣:「人是一種動物,懸掛在他自己用意義編織出來的網上。」「文化就是那些網。」「因此文化的分析是一種詮釋,旨在尋找意義;而不是一種實驗科學,旨在尋找定律。」
然而要解讀這一張意義的網絡,一點也不容易。他在〈厚描〉中以自己田野日誌中的一段紀錄為例,說明這個工作有多麼地複雜、困難。
這是一九六八年他在摩洛哥進行田野考察時寫的,紀錄著發生在一九一二年的一系列相關事件。當時法國剛剛跟摩洛哥的蘇丹簽訂《費茲條約》(Treaty of Fes),取得摩洛哥的主權,並將它納為法國的保護國。摩洛哥的許多柏柏爾族(Berbers)部落認定蘇丹背叛了摩洛哥,因而不同意《費茲條約》的有效性,甚至以武力反抗法軍。為了宣示主權,法國軍隊進駐摩洛哥後,經常找通曉柏柏爾族語的猶太人帶路,去弭平動亂。有些柏柏爾族人因而遷怒這些猶太人,再也不承認他們跟猶太商販簽訂過的貿易保護協定。
在這個背景下,紀爾茲的田野日誌裡寫著:「法國部隊(報導人說)當時初到此地,他們設立了二十個左右的要塞,分布在此地、鎮上、馬爾穆莎(Marmusha)地區的半山腰和沿海的岬角上,以便監控郊區。即便如此,還是無法確保當地的人身安全,尤其是在夜裡。所以,盡管既往貿易協定下的保護制度依法已經被廢止,實際上它們卻繼續存在。」「某夜,馬爾穆莎區一個通曉柏柏爾族語的猶太人科恩(Cohen)還沒睡,兩個在鄰近部落裡買賣的猶太人過來向他購買貨品。附近一個部落裡的柏柏爾族人想要強行闖進科恩的屋裡,但是科恩對空鳴槍警告。(傳統上,猶太人不被允許攜帶武器;但是因為時局動盪,許多猶太人照樣無視禁令而攜帶武器。)這個舉動引起法國人的注意,柏柏爾族人隨之逃逸。」
這兩段文字讀起來就像是純屬事實的客觀紀錄。接下去的四段文字讀起來依然如此。它們說柏柏爾族人第二夜又回來,以詭計成功地闖進科恩的屋裡,殺了那兩個來訪的猶太商販,劫走屋裡的貨品,然後放火焚屋,科恩則勉強逃脫出來。科恩到鎮上包紮好傷口後,去向當地的指揮官杜馬丁上尉陳情,說要帶著跟他簽訂過貿易保護協定的一個柏柏爾族部落去向盜匪索討四、五倍於被劫貨物的賠償。指揮官說依法他不能授權給科恩,只能口頭上同意,但是卻又拋下一句話:「如果你被殺,那是你的問題。」於是科恩帶著他的柏柏爾族人,朝那個劫奪他貨物的柏柏爾族部落出發。最後,兩個柏柏爾族部落和科恩達成協議,允許他從殺人劫貨的部落裡帶走五百頭羊。當科恩帶著羊群回到馬爾穆莎地區時,被法軍發現,指控他是柏柏爾族叛亂區的奸細,並且在監禁他數天之後,沒收他的羊群而釋放他。科恩後來去向當地最高階的上校指揮官申訴,這位指揮官說:「我什麼也不能做。那不是我的問題。」
這六段田野紀錄其實充滿疑點,首先是整個事件只有科恩的觀點,而柏柏爾族人和法軍或許會有全然不同的理解。殺人盜貨的柏柏爾族人有可能是把科恩看成法軍的奸」,「殺人劫貨」只不過是對他的薄懲與示警。法軍可能有他們自己的政治考量,因此當科恩以為他已獲得杜馬丁上尉的默許時,那可能只是他的理解,而非上尉的本意。
如果想要還原事件的完整面貌,紀爾茲說:「釐清的工作將始於區隔當時情境裡三個互不相類的詮釋架構裡的成分,猶太人、柏柏爾族人和法國人;然後才能進而釐清這三群人同時出現在當時的時空情境裡如何(以及為何會)形成一種局勢,讓系統性的誤會發生,使得傳統的互動模式變成社會性的鬧劇。」
然而在這個釐清的過程中,人類學家不能只仰賴田野紀錄裡的「事實」或「資料」,更要借助於自己專業性的分析、推測、想像與批判性的思考,才能從各種可能的版本中選出一個最具說服力的。譬如,根據報導人的說詞,科恩依據過去的貿易協定而要求索賠,跟他簽訂過協定的柏柏爾族也願意幫忙,而法國人卻必須否定過去的貿易協定來宣告主權的轉移和法國統治上的權威。然而科恩明知法軍沒有能力維護鎮外的安全,為什麼他不乾脆搬進鎮上先度過混亂的時局?他明知貿易協定在法軍的官方立場裡是已經作廢的,為什麼還要去跟杜馬丁上尉爭取認可,且最終還去跟上校指揮官陳情?而有些法軍在亂局中確實對猶太商販與柏柏爾族人的恩怨佯裝不知情,那麼馬爾穆莎地區的法軍為何不任隨科恩帶走羊群,而硬要出面扣留羊群?反之,法軍也可以硬把科恩當奸細或劫羊的不法之徒而繩之以法,且兩面手法地藉故去鎮壓劫貨殺人的柏柏爾族,以便趁機伸張法國的主權。而且,根據紀爾茲當年在摩洛哥所做的田野調查,類似的情節都曾在那個主權轉移過程中發生。當我們對當地所發生過的事件了解得愈多,對背後每一個人可能的行為動機設想得愈多,「事實」就變得越複雜、模糊而難以斷定。
就像紀爾茲提醒讀者的:「被我們稱為『田野資料』的,實際上並不直接等於當地人真正的意圖,而是當地線人對他自己及其同胞的意圖所完成的建構,而且又經過我們的再建構。然而在已完成的人類學著作中,前述事實卻隱晦不彰了。原因是,不管我們想要理解的是一個特定的事件、儀式、風俗、觀念或者其他事物,在我們有能力直接檢視它們之前,它們都只是被間接影射的背景資訊。」
接著,紀爾茲以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為例,說明文化分析與小說創作的異與同。福樓拜從一個真實的社會事件出發,靠著想像去揣摩醫師夫人的內心活動(她的夢想、慾望、厭倦與絕望),從而創作出法國文學史上第一本刻畫人物內心的小說。人類學家的工作則是從報導人轉述的事件出發,去揣摩猶太商販科恩、柏柏爾族人與法國人的心思,試圖解釋他們的行動意涵(科恩是「劫羊」還是「索賠」,侵入他屋裡的柏柏爾族人是「殺人劫貨」還是「薄懲示警」等)。
就此而言,人類學的工作跟福樓拜的小說都是從具體事件延伸出去的想像,或者說人類學的分析是對於社會事件的理解與「詮釋」。而且,如果唯有當地人才有資格對當地所發生的事進行第一手的詮釋,那麼人類學家的工作就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詮釋。
然而人類學的「詮釋」與想像又不同於小說: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不需要在情節上忠於啟發他的那個社會事件,也不需要讓讀者認同小說中的情節設計;人類學者的詮釋卻必須吻合實際發生的事件,而且他們的詮釋還要經得起同儕的推敲,對他們而言具有充分的說服力。在這個意義下,小說是文學創作,而人類學的分析則是實證科學。
換個方式說,人類學的田野日誌只是關於一系列事件的「薄描」(thin description),它是關於事件最淺層表象的素樸紀錄;而人類學家對於這些記載的想像、推測、分析與詮釋則是「厚描」(thick description),它企圖刻畫事件更深層的線索與脈絡,使描述變得更豐厚,也讓原本看似詭異或充滿疑點的事件變得可以理解。然而在這個詮釋的過程中,人類學家必須排除缺乏依據的、任性的主觀想像,力求週延、細密而具有說服力,以便經得起同僚的質問與其他版本的競爭。
「薄描」與「厚描」這兩個詞是紀爾茲從牛津的分析哲學家萊爾(Gilbert Ryle)那裡借來的。然而他並非按照萊爾的原意在使用這兩個詞,而是借過來之後施以複雜的加工,使它們變成吻合人類學工作實況的術語,之後才開始應用。因此,紀爾茲的「薄描」與「厚描」截然不同於萊爾「薄描」與「厚描」,有必要先加以釐清。
「薄描」與「厚描」:兩種概念的混淆與釐清
讓我們先看萊爾原意下的「薄描」與「厚描」。他在〈思想的考察:羅丹的「沉思者」在做什麼?〉一文裡指出:表面上相同的動作可能有著不同層次的涵義。他以「眨眼皮」為例,舉出四種不同的可能性:第一個男孩不自主地眨了一下眼皮,只有動作而沒有任何含意義;第二個男孩用「眨眼皮」向某人表達一種「暗示」,藉此傳遞某種訊息;第三個男孩用誇大的滑稽模樣去模仿第二個男孩的「暗示」,藉以取悅旁觀者,這是「模仿暗示」而非「暗示」;第四個男孩在演練前述的滑稽模仿,身邊沒有任何觀眾,這個動作的含意又跟前三者都不同。萊爾接著說:假如有人看見第四個男孩的動作,說他是在「眨眼皮」,這個描述不能說是錯的,然而卻是最極端、最膚淺的「薄描」;在最極端的「薄描」下,四個男孩的動作會因為同一個描述而被誤以為都有相同的意涵。對比下,如果有人把第四個男孩的動作說成是「演練一種關於暗示的滑稽模仿」,這是層次最完整的「厚描」;當四個男孩的動作都被完整地「厚描」時,就可以清楚分辨每一個動作背後的意涵。
萊爾的案例極為完美,不同層次的行為與意義界線分明,吻合集合論的「一一對應」關係。他甚至把這種關於行為的解讀想像成有如電報的譯碼。然而紀爾茲卻批評說,人類學的工作距離這種完美案例太遙遠,而萊爾關於「譯碼」的想像則距離人類學更遙遠。
以科恩的劫羊事件為例,他的言行既涉及他個人的想法,也涉及柏柏爾族人和法國人的行為與想法。如果沒有《費茲條約》和法軍的進駐,這事件可能不會發生,至少其面貌會完全不同;如果柏柏爾族人沒有反對《費茲條約》,這事件也很可能不會發生。此外,科恩對這整個事件有他自己的解讀,柏柏爾族人和法國人又有他們自己的解讀,這三群人各自的想法與彼此的解讀(意義網絡)相互衝撞、交織之後才會出現這一系列的事件。這種複雜編織的意義網絡已經讓事件的解讀極其困難,再加上許多當事人早已不在人世(譬如寄宿科恩家的兩個猶太商販),想要挖掘出完整的「真相」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紀爾茲說:「人類學的工作就像在閱讀一份手稿,它來自陌生的遠方,筆跡已經褪色而不易辨認,充滿脫落的文句與前後不一致的敘述、可疑的修改痕跡和立場鮮明或帶著偏見的評論;只不過這個劇本不是用慣常的圖表和語言寫作的,而是用轉瞬即逝的行為模式撰就的。」而且「民族誌的研究者所面對的是多層次的複雜概念結構,這些概念結構經常彼此疊加在一起,或者彼此交纏地被編織進對方的結構裡,同時它們顯得既怪異、不規則,而且又隱晦不明;民族誌的研究者必須先設法掌握住這個結構,之後才能將它解譯。」
緣此,在人類學的工作裡,討論版本的「對」與「錯」是沒有意義的。與其說人類學的分析是像萊爾想像中的「譯碼」,不如說人類學的分析更像是在解讀一九一二年發生在摩洛哥的一齣行動劇,或者在詮釋莎士比亞的一個劇本——當你面對同一個劇本的兩種不同詮釋時,只能討論「哪一個版本的解讀比較週延、詳盡、細密而有說服力」,而不能討論「哪一個版本的解讀才是正確的」。
因此,當紀爾茲說「民族誌就是厚描」時,他的「厚描」跟萊爾的概念是明確地區隔開來的:「所謂的分析就是要釐清意義的結構,然而當萊爾把這工作稱為『解碼』時,多少有些誤導,因為他把釐清意義結構的工作想像得太像電報的譯碼,而真正的工作更是是文學評論,以及決定它們的社會背景和重要性。」「關於滑稽的眨眼和滑稽的劫羊,要問的不是它們所對應的本體論層次,而是它們在特定的處境與作用下究竟想要說的是什麼樣的訊息:是企圖讓某個動作顯得可笑或有難度,是諷刺還是氣憤,是勢利或者自豪。」
務實地說,「文化分析是(且應該是)猜測可能的意義,評估我們的猜測,從最佳的猜測找出解釋性的結論;而不是去發現『意義的大陸』,並且將那個抽象世界裡的地形起伏給精確地描繪出來。」
文化人類學的可能與不可能:一個獨特而無可取代的任務
維根斯坦曾說:「如果獅子會說話,我們將無法理解牠。」關鍵在於:我們無法站在牠們的立場去看待與感受牠們的世界(無法「感同身受」)。
紀爾茲也引述維根斯坦一段類似的話:「重要的是,有些人讓他人感到極端費解。當我們進入一個傳統迥異的陌生國度時,就會了解這個事實;更重要的是,即便精通當地語言,依舊如此。我們無法了解當地人(原因不在於聽不懂他們彼此的對話)。因為我們無法跟他們有完全一樣的觀點和感受。」或者說,除非我們從小就在某個特定的文化薰陶下長大,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感同身受」地擁有該文化所薰陶出來的「世界觀」。
想要去同理異文化,盡可能感同身受地體驗他們的生活方式與世界觀,這一直都是人類學研究的終極目標,雖然人類學家始終離這個目標非常地遙遠。就紀爾茲的個人體會而言,人類學家的終極目標並非成為當地人的一員,也不是企圖模仿他們的言行與思考,而只是試圖跟他們建立起對話的可能性,或者說促進異文化的對話。當人類學家的努力使得異文化的對話管道日益暢通時,彼此的曲解、誤會乃至於無心的傷害就有機會減少。
然而人類學家對異文化的詮釋最終仍只是一種「詮釋」,永遠不會等於當地人對自己的理解或詮釋。越是清楚地自覺於此,越能避免因為過度自信而引起的誤解。
其次,紀爾茲非常強調人類學的「微觀」特質。當人類學家面對摩洛哥的猶太人、柏柏爾族人以及法國人時,他也像其他學科那樣地關心當地人的「權力、改變、信仰、壓迫、工作、熱情、權威、美、暴力、愛、特權」等不同社會的普遍問題,只不過他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不同於注重宏觀理論的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與史學。
人類學家把研究聚焦在特定時空情境與特定文化、歷史脈絡下的具體事件(譬一九一二年在摩洛哥馬爾穆莎地區的劫羊事件),原因在於這是回答某些問題的最佳方式,譬如「法軍進駐摩洛哥對猶太人與土著原有貿易協定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殖民統治對土著的自尊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或者「殖民地統治對當地的道德規範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用紀爾茲自己的話說:「人類學家的材料來自於長期的,主要是質性的(偶有例外)、高度參與的、近乎強迫症般地精細梳理過的田野研究。有了這些材料,讓當代社會科學苦惱不已的龐大概念(譬如合法性、現代化、融合、衝突、超凡的個人魅力、結構、意義等)獲得可以被感受的具體真實性,我們才有可能真切且具體地去思考它們,更重要的是還可以運用它們進行創造與想像。」
人類學當然也會像其他學科一樣,嘗試著將其研究成果予以理論化,尋找不同案例之間的共通性,以便擴大其研究成果的適用範圍。在這過程中,理論的「前後一致性」固然重要,然而「事實」還是比「一致性」更重要。
那麼,當人類學家堅持著「具體的」、「微觀的」事件與細節時,會不會妨礙他去建構比較具有普遍性的理論?紀爾茲說:確實如此。然而具體的事件就像滋養人類學的土壤,如果為了理論化(抽象化)而背棄它的話,文化研究就會變得蒼白、失血,甚至虛假。畢竟,每個文化都有它的獨特性;如果忘了這個前提,就等於是否認了人類學存在的必要性。
對具體事件的堅持與理論化的需要是人類學無法掙脫的矛盾:對於具體事件的堅持,使得人類學的理論高度受到限制;兩者之間就像是有一根彈簧連結著,理論化的程度越高,把它拉回土地的力量就越強。紀爾茲最終的結論是:不可能會有「文化詮釋的一般性理論」。
然而這絕不意味著人類學的研究不能隨著持續的累積而日益進步,它只不過意味著人類學的進步方式跟自然科學不一樣。它表現在:基於對個案的研究累積,因而對事件的脈絡有越來越詳盡、豐富的掌握,也可以對個案詮釋得越來越週延、細膩。就像紀爾茲說的:「過去被發現的事實被組織起來,過去被發展的概念被運用,過去被構想出來的假說被拿來驗證;然而發展的方向不是從已經被證實的理論邁向新的理論,而是從笨拙地摸索著最起碼的理解邁向有充分根據的主張,並且繼續邁向更週延、詳盡而有說服力的詮釋。」
那麼,人類學研究的終點在哪裡?永遠沒有終點,至少對紀爾茲而言,「文化分析的固有特質就是永遠沒有完成的那一天。」而且「你挖得越深,它越顯得不完整。」「你越是覺得對手上的材料有所理解,越是會因而強化你自己和他人的懷疑,覺得似乎有哪裡不太對勁。」而這就是人類學家的工作。
這位著名人類學家成熟期的證言是不是有點悲觀?如果認真追憶一九三◯年代以來物理學與經濟學一再發生的觀念革命,人類所有學科的進步不都是沿著這樣的軌跡前進嗎?甚至於學術界所謂的「批判性思考」,不就是始於「自我批判」嗎?
或許,與其說人類是在「追求真理」,不如說人類是在不斷地創造他對這個世界與自我的想像(理解、詮釋),且不斷地質疑自己的想像,因而在這過程中加深對自己的認識,也日益警覺到自己的無知和多麼容易被不自覺的「想當然爾」所欺矇。
巴厘島的鬥雞:人類學「厚描」的經典代表
要掌握紀爾茲思想中的「厚描」,〈深層遊戲:關於巴厘島鬥雞的記述〉 是一篇不可不讀的經典代表。這篇文章讀起來趣味橫生,乍看迥異於學術期刊的論文,尤其第一節的「突襲」描寫警察臨檢的過程,既是親歷其境的田野訪談紀錄,又像偵探小說般地驚險、刺激、充滿意料之外的轉折。然而如果去除掉文學性的成分,這一章兼具一般學術論文理「導論」的功能:它說明作者從不被信任的「他者」身分如何轉化為被當地人接納的「我族」,以及作者觀察與研究峇里島鬥雞的角度(身分)如何有別於既往的研究者,同時它也藉此暗示這一篇論文何以有機會揭露既往論文所不曾揭露的訊息。此外,它也含蓄地批判了傳統人類學對研究者的告誡:作為客觀的觀察者,盡可能有如透明人般地不去攪亂當地的互動與既有秩序。因為,當他恪守傳統人類學的觀察方式時,他無法從當地人聽到任何「在地的第一手詮釋」;直到他跟當地人一起逃避警察的追緝,還跟當地人一起說謊來包庇村長,之後他才開始有機會聽到當地人的第一手詮釋。
第二節「鬥雞的與男人的」一開頭就指出:峇里島的神話、藝術、儀式、社會組織、孩童教養等,能想到的各方面課題幾乎都已經被無微不至地詳盡研究過了,唯獨鬥雞是個例外。然後他用自己的觀察與第一手聽聞去凸顯鬥雞這種遊戲在峇里島社會中罕見的重要性,接著引述前人有關峇里島鬥雞的觀察與詮釋,以及他對這些觀察與詮釋的強烈質疑,最後是描述一些費解的激烈舉動(譬如,在重要比賽中落敗的人有時候會搗毀祖先的神盦、詛咒諸神,有如形上學意義或社會意義上的自殺)和待解的謎團。經過這些鋪陳,本研究的主題、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以及既有研究的不足隱約可見。然而敘事的筆調鬆散,而不像一般期刊論文的導論那麼緊湊;即便是評論的時候也隱微含蓄,不會太露骨或咄咄逼人。
第三章的標題是「戰鬥」(The fight),它詳盡地刻畫鬥雞場內兩隻雞的裝備和打扮,接著是兩隻雞血淋淋的廝殺過程,再輔以對遊戲規則的解說,讀起來就像是親臨其境地在觀賞一場鬥雞比賽。如果用紀爾茲的術語說,這一節是有關兩隻雞相鬥過程的「薄描」或單純的田野紀錄,因為它只有客觀現象的精細描繪,而沒有人類學的剖析、解讀和詮釋。
第四節的標題是「賠率與勝算」,它把田野紀錄的焦點從雞隻身上轉移到四周圍觀的人群,以及他們的賭局,並鉅細靡遺地刻畫賭注賭局的規則與群眾的情緒變化與不可思議的投入程度。然而這依舊只是純現象性的「薄描」,而沒有更深層的分析。
第五節的標題是「玩火」,它一開始就指出來:把龐大的金錢與社會地位押注在一場鬥雞裡,對於參賽的雙方都是幾近玩火、嚴重違背理性算計的行為,然而峇里島人卻樂此不疲,甚至甘願冒著違法而被警察取締的風險。接著他引述峇里島人的話,說鬥雞不只是看熱鬧和金錢的賭博,更是涉及榮譽、屈辱、自尊、敬重與社會地位的賭注,是一場「深層的賭局」和「深層的戲碼」。接著,他深入峇里島人的風俗、習慣與社會結構,分析他們為何要在鬥雞的活動裡豪賭自己的尊嚴與社會地位,並且引用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理論說:峇里島的鬥雞表面上沒有任何人會受到肢體的傷害,一般人的金錢賭注也不大,然而實質上卻是攸關自傲與尊卑的「社會地位的浴血戰」。最後,他把鬥雞賽背後社會默認的共同規範做了一個條列式的總整理,譬如:當地人會感受到一種壓力,必須押注在跟自己的血緣較近的這一方,以示對族群的忠誠;同時還要藉此表示你地位再高都不會高到看不起自己的親族。然而這主要是當地人對鬥雞賽的詮釋,頂多只是第一層的「厚描」。
第六節的標題是「羽毛、血、群眾與錢」,它指出峇里島的鬥雞之所以會引起如此大的不安,是因為它同時具有三個層次的意涵:「它表面上的戲劇形式,它的隱喻內涵,以及它的社會脈絡」。換個角度說,它「把自傲與自我給綁在一起,把自我與鬥雞給綁在一起,然後又把鬥雞跟毀滅給綁在一起」。通過鬥雞過程的隱喻與想像,它也把把峇里島人一向被種性制度所壓抑的情緒(嫉妒、血腥、兇狠等)給釋放出來,猶如把峇里島人被儀式、委婉措詞、繁文縟節等習尚遮掩起來的一個面向給實現了出來。因此,鬥雞在峇里島社會的功能就像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李爾王》或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罪與罰》,它們通過藝術表現的形式實現了那些我們不敢在現實世界裡實踐的情感與禁忌(對於自己、他人或者社會的結構、文化與習尚等),讓我們的內心獲得某種滿足。因此,紀爾茲說:鬥雞是「峇里島人說給自己聽的故事」,是峇里島人對其生活世界的「詮釋」。這一節完全是人類學家的詮釋,是比第五節更深一層的「厚描」。
最後一節(第七節)的標題是「關於某些事件的言說」,它才是這一篇論文最後一層的「厚描」。它一方面是從鬥雞賽的表象去詮釋當地人內心最深層的感受,一方面把他在峇里島看見的人性展演跟歐洲戲劇、小說中的人性展演關聯起來,進行異文化的對話。譬如:當峇里島人以鬥雞主人或下注者的身分積極參與鬥雞遊戲並一再觀看後,「他逐漸熟稔它,而鬥雞對他敘說的,有如弦樂四重奏對專注的聆聽者,或者靜物寫生對沉浸於其中的觀賞者,他們逐漸地熟稔它們,而它們則為觀賞者開啟他們的內心世界。」因此,峇里島的鬥雞就像原始社會的文化、敘事,跟進步社會有著許多雷同之處——峇里島人看鬥雞,就像莎士比亞的觀眾在看馬克白。或者像亞里斯多德詩學的主張,文學是刻畫人性中永恆不變的特質;不管是馬克白或迭更斯的小說,閱讀的目的不是去了解不可重複的歷史,而是設法了解人性中永恆不變的質素。
這一篇關於鬥雞的論文讀起來像是報導文學,或者峇里島行動的分析與評論,比〈厚描:朝向文化的詮釋理論〉更不像社會科學的論文,也更具有文學與散文筆調的魅力。然而它的結構依舊是層次井然:它先聚焦於鬥雞場內的客觀事實,繼而是場外的人群與賭局,之後是當地人的詮釋和解讀,以及人類學家的詮釋和解讀,最後是兩種文化的對話,以及文化研究與性的關係。此外,它也有許多明確的主張(尤其是在最後一節),不乏對既有文獻的批判,還準備了豐富的證據(田野紀錄)、詳盡的分析和委婉的討論,表面上娓娓道來,骨子裡終究藏不住說服的意圖。
撇開筆調與寫作風格的差異,〈深層遊戲:關於巴厘島鬥雞的記述〉依舊扣著著「去蕪存菁,精準表達,以理服人」的學術旨趣。若進一步深究,使它風格上迥異於其他社會科學的根本因素,是研究性質的差異:至少在紀爾茲看來,文化人類學追求的不是客觀的真理,而是對於異文化一系列相關事件的分析與詮釋,以及異文化之間的對話。
散文風格的另類批判:「以理服人」的另一種典型
文化研究確實有它獨特的目標和屬性,不只迥異於自然科學,也跟其他社會科學有著鮮明的差異。然而這絕不意味著「去蕪存菁,精準表達,以理服人」的技藝全然不適用於文化研究或人類學的寫作,更不能說文化研究或人類學的寫作與批判性思考無關。
以〈厚描:朝向文化的詮釋理論〉為例,盡管它的筆調從容、優雅,風格酷似散文或創意寫作(creative writing),而迥異於常見的「學術寫作」,然而文中不乏對人類學界既有主張的針砭與批判。此外,「原創性」與批判性思考依舊是它之所以為學術界津津樂道的關鍵要素,也是紀爾茲的關鍵性寫作旨趣。
它經常使用複雜的分詞構句,一個句子往往長達五行,語意經常在肯定與否定之間迅速反轉,措詞往往委婉到讓讀者不易拿捏。盡管這種風格讓文章顯得活潑、優雅而不刻板,卻也使得習慣於直白英文(plain English)的研究生和中文翻譯者備感吃力,甚至暈頭轉向。然而如果仔細玩味,這些複雜的句型結構絕非為了炫耀寫作技巧,而是為了精準的措詞。對於能習慣其寫作風格的讀者而言,這樣的寫作風格可以增加一點閱讀的趣味,破除「學術寫作」與「創意寫作」之間的藩籬,也間接反應「文化研究本質上橫跨文學與實證科學」的主張。而文中所舉的案例與證據都潛藏匠心,表面上是信手拈來,實際上絕對是一絲不苟的認真篩選。也就是說,「去蕪存菁,精準表達」的原則只不過是以更具文學性的方式呈現,而不是被廢棄或貶抑到次要的地位。
最後,盡管這兩篇論文對前人的批判都迂迴含蓄,甚至不著痕跡;然而它也絲毫不曾苟且地放過任何該批判之處,只是在批判與表述主張時筆調較柔軟而已。這種筆調的柔軟雖然跟修辭有關,更重要的卻是因為文化的詮釋本來就比自然科學的結論具有更高的不確定性;在「證據到哪裡就論證到哪裡」的原則下,文化研究的結果必然是調性偏軟的。
盡管如此,紀爾茲的論文依舊充滿著啟迪後生與同儕的企圖,或者說軟性的說服力量。尤有甚者,如果從這兩篇文章在人類學界與文化研究領域的深遠影響來看,它們的說服能力之強,絕不下於任何社會科學或理工領域的經典之作。
不過,這一點絲毫也不足稱奇:如果你不期待讀者的認同,哪有可能會費盡心思地寫論文,還從中遴選,編輯成書?